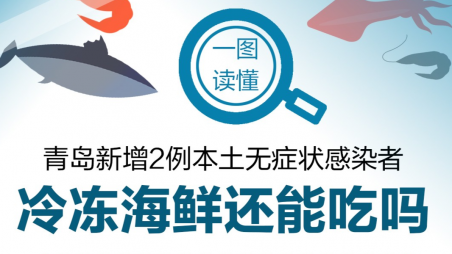2020-10-05 12:44
1939年,山西吉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叫井圪塔(或井疙瘩)的小村庄,发生了一件惨绝人寰的血案。从1月1日到1月4日,几十个日本鬼子多次前来这个仅有11户普通农民、仅剩30余名老弱妇孺的井圪塔村,进行掠夺和杀戮。躲进村后沟底崖壁上的藏身洞里的村民,利用地形的优势,用手中的石块、铁锹、菜刀和剪子,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杀死杀伤十余名敌人后,最终因没有武器的劣势,被敌人攻入藏身洞。30名老弱妇孺,除了两名被父母压在身下的女孩和一名受重伤的14岁男孩(逃出报信后不久也因伤身亡),其余27人当场遇难。

▲1994年山西省吉县井圪塔村立的《井圪塔抗日英烈纪念碑》卢任民 摄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像井圪塔这样英勇抵抗的村庄不计其数,为何井圪塔这个名字没有被历史长河所湮没?主要源于井圪塔的英烈事迹当时被广泛报道,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地激起了全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当时,井圪塔村民英勇抗敌的事迹被一次追悼会,一部报告文学以及一部电影详细地记录下来,这才有了现如今立于村头的两座纪念碑,它们时刻警醒着后人。井圪塔村民们的血没有白流。
1938年,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李公朴,为了宣传山西的抗战业绩,几次来到山西考察。他在吉县呆的时间比较长,完成了《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一书。
就在李公朴身处吉县期间,井圪塔血案发生了。1939年1月9日,井圪塔日军杀害烈士追悼大会在吉县县城城隍庙召开。会上,人们展出了烈士血衣以及与日军搏斗的刀刃等实物。李公朴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演说。
会后,李公朴应吉县县长的请求,为28位烈士(日寇当场杀害27人,加上逃出报信后死亡的1人,共28位)撰写了近千字的碑文。李公朴在1939年2月20日写于吉县的《两渡黄河》一文,记录了当时写碑文的细节:
“县长燕尧松嘱为碑文亦表扬二十八烈士之悲壮事迹。兹录之于后,以见此惨剧之经过与其给予吾人之教训又是怎样的深刻!……
民国念(廿)八年一月一日,日寇再犯吉境,到处烧杀掳掠,县西南六里外,井圪塔村,有一异常荫蔽而又险峻的山窑。亦同遭浩劫。初则尽其财物搜刮以去,继续率众前往,再图掳掠,居民不甘受敌欺辱,遂竭土块锅碗,据险抵抗,坚持达三日之久,毙敌六人,伤敌无算。第四日敌寇竟续增百余人。猛烈攻击。终以赤手空拳,土块俱尽,致被攻入,三十二人,除四幼童因窑内黑暗,被其母压伏晕厥得以幸免外,皆惨遭杀戮,血肉满山窑,其中妇女三人曾强被掳出,然以不求苟免,沿途反抗终于被戕,尸坠山沟。冲发握拳,状尤悲惨!此种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奋斗到底的精神,实足以使顽夫立懦夫强,增添了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李公朴的发言以及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杀敌的士气。这些文章收入李公朴的《战地通讯》中,也使得后人们能够铭记先烈的英勇事迹。
除了纪念文章,还有记者撰写了报告文学。1939年初,24岁的萧殷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派遣,从延安前往晋西协助李公朴工作。在吉县他听说井圪塔村被日军扫荡的惨案后,第一时间他到井圪塔村采访。2月23日,他写下了报告文学《井圪塔的血》,讲述了手无寸铁的村民与手持机枪的日寇搏斗到最后,全村村民几乎灭绝的实况。文章写好后发给了共产党大型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3月23日至25日,《新华日报》连载了署名为“萧英”的报告文学《井圪塔的血》,文章不仅唤起国人奋起抗日的决心,也令井圪塔这个在中国版图不易被发现的小村子,没有像其他千百个惨遭同样命运的小村庄那样,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1984年,《萧殷自选集》中收入了《井圪塔的血》一文。
1939年,著名导演沈浮(1905-1994,曾执导过《北国江南》、《老兵新传》等影片),读到报告文学《井圪塔的血》后,深受震撼,他根据报道的内容,编写了电影剧本《老百姓万岁》(又名《大地烽烟》),后来该电影由西北影业公司摄制,沈浮为编导,陈晨为摄影。当时摄制组还远赴山西黄河沿岸进行外景拍摄。不过,可惜的是,拍摄这部影片的西北影业公司是阎锡山出资创办的,当影片拍摄完成80%的时候,公司被阎锡山下令停办,电影因此而夭折。

1939年3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井圪塔的血》第一部分 陶萌萌 供图
尽管电影没有拍摄完成,但是井圪塔村的英勇事迹没有被遗忘。新时期,为了让后代子孙铭记先辈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事迹,山西吉县人民政府以及该地区的小学师生在井圪塔村的村口竖立了两座纪念碑。一座是1994年立的《井圪塔抗日英烈纪念碑》,另一座是2000年立的《井圪塔人民抗日遇难纪念碑》。
在《井圪塔抗日英烈纪念碑》背面,刻有碑文详细记录了当年井圪塔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以及日本侵略者屠杀村民的血腥暴行。碑文也提到了李公朴为村民举办追悼会以及萧英撰写《井圪塔的血》这篇文章的历史。
听村民们讲述,几年前,井圪塔惨案的幸存者白梅梅离开了人世。在她去世前的几年,她经常来到村头,在纪念碑前久久伫立。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她想到了什么?也许,在怀念逝去亲人们的同时,她还带有一些遗憾。也许她在遗憾当年李公朴先生撰写的碑文不见踪影;也许,她在遗憾再也没有见到当年那位采访过她并写出《井圪塔的血》的八路军叔叔;也许,她遗憾一直没有看到根据《井圪塔的血》拍摄的电影《老百姓万岁》……
带着这些遗憾,她走了。
如今,后来者的一系列努力,可以告慰白梅梅和井圪塔血案中牺牲的英烈们:井圪塔村民们的血,没有白流。
萧殷的后人在2015年10月代表萧殷(萧殷已于1983年去世)到纪念碑前进行了拜祭,并把《井圪塔的血》的文章以及1939年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刊登该文章的影印件交给了吉县县委宣传部;李公朴所写的碑文近日也在《李公朴文集》中被找到,人们得以重温当年村民的英勇事迹;《老百姓万岁》这部珍贵的影片资料,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国家片库里。
当然,在抗战胜利七十五周年之际,后人们还有更多期盼:期望刻有李公朴所写碑文的纪念碑,能竖立在英烈牺牲的地方;期待《老百姓万岁》这部珍贵的影片,能以独特的方式与广大观众见面。
补白
“萧英”变“萧殷”引出一桩文章迷案

身穿八路军装的萧殷。1939年5月14日摄于延安,萧殷从吉县回延安没多久。陶萌萌供图
几年前,笔者的一位老同学陶萌萌,写了一篇文章:《重返井圪塔》。文章讲述了她的父亲萧殷1939年在晋西采访吉县井圪塔村村民英勇抗击日寇,并根据采访写成报告文学《井圪塔的血》的事。
《重返井圪塔》还提到,2015年10月29日,作为萧殷的后人,他们前往吉县,专门到井圪塔村,拜祭抗日英烈的英灵。他们在村口看到了前文提到的两座纪念碑,其中一座碑的碑文也提到“肖英撰井疙瘩的血”一事。
值得一提的是,当他们专程去井圪塔村后得知,当地政府一直找不到《井圪塔的血》的原文,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曾经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更想不到当年那位八路军记者的后人会找上门来提供重要史料……
碑文中提到了“肖英撰井疙瘩的血”,而且这篇报告文学,被收入了1984年出版的《萧殷自选集》,为何吉县政府找不到这篇原文呢?
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这里面有一个看似复杂,稍微考证就能明白的问题,那就是“萧殷”与“萧英”的关系。
对文艺界人士来说,萧殷并不陌生,萧殷原名郑文生,曾用“萧英”的笔名发表文章。1936年10月,年仅21岁的郑文生以“萧英”的名义写信给鲁迅并寄上自己的散文《温热的手》。鲁迅先生因病重未能复信,但在1936年10月9日的日记中记道:“得萧英信并稿”。
根据重庆《新华日报》当年发表报告文学《井圪塔的血》时的资料,这篇文章使用的名字也是“萧英”。
那么“萧殷”这个笔名又是何时、因为何故开始使用的呢?
1946年2月,《解放》报“三日刊”创刊,时年31岁的郑文生(萧英)奉命到北平《解放》“三日刊”负责对外采访任务。他参与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军三方组成的军调部的采访工作。
当年3月,萧英写了《〈解放三日刊〉创刊前后》一文,寄回解放区《晋察冀日报》,揭露国民党特务压制民主的恶劣行径。考虑到作者身在北平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发表此文时,《晋察冀日报》报社领导决定用“萧盈“为笔名。受此启发,不久以后,《解放》报社再印名片时,萧英使用了“萧殷”这个名字。从此以后,萧殷就成了他的正式笔名。
笔者曾经几次拜访过萧殷,萧殷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客家口音。而笔者恰巧也是客家人。在客家话中,“英”和“殷”的发音完全一样,或许这就是萧殷决定使用“殷”字的由来。
“萧殷”这个笔名,从1946年开始被使用,并取代了其它的笔名。此后,这个名字为中国文艺界所熟知,许多文艺界人士可能不知道郑文生,不知道萧英,但会知道萧殷。
这也回答了先前的疑问,为什么吉县政府知道《井圪塔的血》是萧英所作,却找不到原文的原因——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萧英就是在中国文坛享有盛名的萧殷。
(原标题:1939年吉县井圪塔村32位村民抵抗日军 28人牺牲 李公朴写碑文 萧殷写报道)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陈家基
流程编辑:u010
版权声明: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改编。